外界所谓的专业人士对股市的看法,就好像公鸡打鸣预测天气变化一样,对于这样的预测,你会相信吗?
我经常被问及,是从哪里得到信息和主意的。我不是寻找它们,我是获得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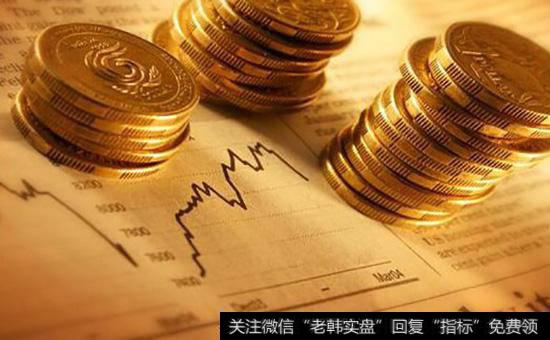
我的回答是很简单的,我担心读者甚至会嘲笑这个答案。我到处都能获得信息,我从各种类型的人们那里获得,从小偷、总裁甚至部长或者妓女那里,也就是说从所有人那里,但不包括银行家、经纪人和分析师这些人目光短浅,或者如人们通常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好是反着他们的建议来做。
在20世纪30年代,我经常逗留在伦敦。在那里,我的一个朋友从另一个匈牙利人口中得到关于伦敦股市的建议。那位匈牙利人现在叫巴洛格勋爵,是工党的财务顾问。年轻的巴洛格当时作为分析师就职于Falk&Co.这家公司的匿名合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勋爵。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本书中我曾对他有所提及。奇怪的是,我通过朋友从这个公司得到的股市消息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尽管凯恩斯勋爵通过成功的投机获得了大量的財富,但很可能不是投机于股市而是投机于各种货币。他投机于印度的卢比、法国的法郎、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并且主要是卖空。他的货币投机总是卓有成效,而他的股市交易的成功很可能就少一些了。除了一次特别的行动:在1929 ~ 1932 年股市大危机期间,凯思斯勋爵在华尔街大规模人市购买股票,这些股票在罗斯福新政下出现了暴涨。这是大手笔的股市行动,因为他认清了大的趋势转变。但是他们在单一股票上的建议是不可靠的。我援引这个小小的事例是为了证明不可靠的消息可以出自最好的来源地。
总裁的消息不一定是真的
很多年以前,一个很好的老朋友思斯特.加尔从苏黎世语气激动地给我打电话,他当时是大银行瑞士宝盛(Julius Bar & Co.)的首席代理人和股市交易员,现在是高盛的苏黎世总裁。他一直都是一个出色的股市专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同事,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认为必须购买圣.莫里茨纸业(St. Moritz)的股票。“为什么?”他回答:“这些股票将会上涨。”
这些股票每股涨了40法郎。我的好朋友尽管没有解释,但他那激动的语调告诉我,他对这只股票的上涨是坚信不疑的。他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行家。我相信他,并按160法郎的价格购买了股票,尽管它们一年前的价格只有40法郎。
当我放下听简时突然想起,这个公司的总裁乔治.赫瑞先生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经常给他的投资提供咨询意见,他以前曾担任南方航空的总裁,卡拉维拉汽车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西姆卡的总裁和克莱斯勒的副总裁。
我问他对这只股票的购买建议和看法,他的回答是令人震惊的:“苏黎世股市上的价格完全是瞎扯。账面价值还不到40法郎,绝对没有分红的希望。这是一种投机的胡闹行为,把价格推到了一个这样的高度。苏黎世股市是疯了,股票在这个价格上只应被脱手,肯定不应被购买。”他回复的激烈程度让我重新对此进行思考。我真的确定,总裁先生是有道理的,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过高。可是我坚信,股市的愚蠢行为是没有边界的。
我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以便给瑞士宝盛的朋友打电话。“我看你是个胆小鬼,没有再买进这只股票.”电话声充斥着我的耳朵:“今天,圣莫里茨纸业已经涨到165了。”能给一个银行家上一课让我很高兴,尽管他是我非常重视的好朋友。我逐字逐句地向他复述了赫瑞总裁告诉我的消息,以及我自己对此的确认。电话线的那头传来胆怯的声音:“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你想重新卖掉吗?”
“我们应该做什么?你给我继续买进圣莫里茨纸业。”紧跟着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看见我的朋友变成了我面前无声的问号。我补充道:“我只是想向你展示,我给资产负债分析和内幕消息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即使这些消息来源于总裁。”
第二天,我在定期聚会上向我的朋友们讲述了这个古怪的决定,并且他们可以作为证人。然后我忘记了整个的事情。几个月后,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关于圣.莫里茨纸业的报道,它的股票刚刚从1200法郎跳跃到了I600法郎。我重新给苏黎世的朋友打了电话,很高兴地卖掉了我所有的圣.莫里茨纸业股票。
当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交易已执行时,我开玩笑地问他:“怎么样,亲爱的朋友,我的主意好吧?”他非常“受伤"地回答道:“为什么是你?这可是我的主意!”(他这么说也不无道理.)
“买?不,卖”还是“买,不卖”
一段时间以后,圣.莫里茨纸业还上升到了更高的价位,然后它在股市中消失了,因为它被一家英国公司鲍沃特(Bowater) 高价收购了。几年后,我同赫瑞总截谈起此事,我们大家由衷地放声大笑。只是这时候他也知道了他当时不知道的东西:鲍沃特的敌意收购计划。他的资产负债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分析家思考股市决定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