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的价值投资》(Active Value Investing)一书中,作者维塔利•凯茨尼尔森(Vitaliy Katsenelson)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1982年这段充满艰辛的盘整市场行情中,深度价值股则实现了强势反弹,创造了近15%的年均回报率。有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在1970-1983年期间,以根据本杰明•格林厄姆
“净流动资产价值”概念选择的深度价值股为对象的投资,居然实现了近30%的年均收益率。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2000-2009年的盘整震荡时期,在市值不低于5亿美元且权益大于负债的全部股票中,市盈率排名最低的10只股票表现优异,实现了近17%的年均回报率。显而易见,对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者来说,即便是长期牛市的顶部附近,机会依旧存在。
菲利普•费雪和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认为,价值股(低市盈率股票)和成长股(高市盈率股票)之间似乎存在着另一种周期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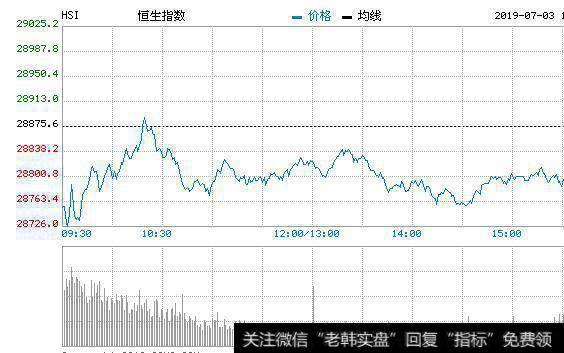
在本质上,价值股和成长股之间往往此消彼长,到底谁占优势,还取决于如下三个因素:
(1)利润增长的动力。当公司盈利增速放缓时,成长股开始变得稀少。因此,收益超过大盘的成长股成为市场的宠儿。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股往往要优于价值股。反之,当公司盈利加速增长时,价值股往往优于成长股,因为成长股已随处可见。
(2)长期利率的走势。成长股很少支付股利,投资者的回报来自于股价在长期内的升值。因此,投资者习惯于将它们与长期债券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很多价值股则支付高股利,并且被投资者短期持有。这意味着,在利率下调时,长期债券的收益率超过短期债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股的回报率要好于价值股;而利率上调时,价值股自然强于成长股。
(3)全球收益曲线的形态。当全球收益曲线变得陡峭时,贷款利润率的改善促使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为价值型公司(负债通常高于成长型公司)的融资提供了便利。这就加速了价值型公司的发展,因此,其股票的收益率往往会超过成长股。当收益曲线变得平缓时,价值型公司会发现,它们的融资难度要超过成长型公司,因而,使得后者的股票收益情况占得上风。
转向更具价值潜力的资产。随着行情的变化,投资者可将股票转换为现金或是股市中被深度低估的其他股票,与此相似,投资者也可考虑将股票转换为更具价值潜力的其他类型资产。显然,只有投资者熟悉的资产类型,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投资对象。乔治•索罗斯等宏观型投资者通常擅长于多种类型的资产(如大宗商品、衍生品、利率工具、货币、股票以及不动产等),因而在所持股票丧失升值潜力时,可以有更多的可选择空间。而对以股票为主的投资者而言,债券自然就成了他们不二的备选对象。
例如,2000年3月(恰值科技股泡沫即将破裂之时),约翰•邓普顿曾投资收益率为6.3%的零息债券,他的理由是,股票在未来10年只能带来微薄的回报,此外,一旦泡沫破裂,美联储就不得不着手防范经济衰退,因此,他预期基准利率将进一步走低。同样,沃伦•巴菲特也曾在2002年大量投资垃圾债券,因为他认为,股票市场将继续暗淡无光(尽管2000-2002年的熊市刚刚结束),而且他坚信,低迷的商业形势必将在债券价格上有所体现(从而提高了债券的收益率)。同样,斯蒂芬•罗米克(Steven Romick)认为,在2008-2009年的信贷危机过程中,高收益债券的价值潜力必将远胜过股票,因为债券不同于股票,经济萧条必然会体现在它的价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