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行为金融的理论,大多数投资者进行决策或选择时,都无法或不愿意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有效市场假说所示的冷静、客观并具有完全信息的方式进行分析。富勒-泰勒投资管理公司的部门选择优于那些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的选择。我们在《投资革命》的第124页和第125页中讨论费雪·布莱克1986年关于噪声交易者的论文时也提到过这类投资者。正如布莱克的描述,噪声与信息相对应。噪声交易者根据他们深信可靠的意见和分析方法来进行买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却使用了错误的信息——错到了极点。1999年3月29日(星期一),Computerliteracy公司更名为fatbrain.com,并在一天内实现其股价36%的上涨,这就是噪声。
大量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必将导致总体资产的错误定价,而这又意味着凡是阅读并领会了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及其继承者著作的行家们都会发财。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变得跟富勒-泰勒投资管理公司的客户一样富有了呢?布莱克在他1986年的论文中以独特的方式指出,“噪声一方面为获利创造了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获利的难度”。
许多投资者或许可以很幸运地在某个时刻击败市场,但“市场”毕竞是所有人行为的一个平均结果,于是总有些人会比市场表现得更好而其他人则表现得更糟。这与经过风险调整后每年持续超越市场表现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记录表明,不管持续多长时间,只会有一小部分人的表现超过市场平均水平。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但是他们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正是因为这祥的投资者实在太少,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的所作所为看起来相当简单,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效仿,然而这些又是难以效仿的。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等到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十分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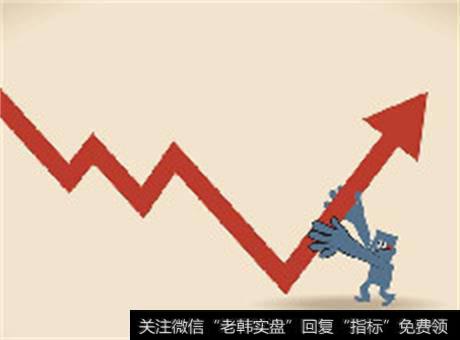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从1977年到1990年,在传奇人物彼得·林奇(PeterLynch)的管理下,富达(Fidelity)的麦哲伦基金实现了超过2700%的增长,即年复利收益达29%。林奇之所以成为传奇人物,是因为没有人与他有相似的成绩记录。林奇总是强调他的选股原则只是常识,即“我的妻子对该公司的产品很感兴趣”,这很容易被其他职业经理人复制。但由于其他的经理人未能复制他的成绩记录,那么这其中的道理一定不只是常识这么简单。
对机构投资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职业经理人在股票和固定收益市场中都表现不佳。共同基金是我们最常见的机构投资群体,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持有人,同时也因为他们必须将其绩效表现公布于众。虽然在扣除费用开销之前,许多共同基金都有超越市场表现的趋势,然而在计算了营业费用、税收、管理费用后,其利润被削减,从而也减少了他们带给持有人的回报。
比如在2006年的9月,在被晨星(Morningstar,一个共同基金调查服务机构)定义为大型增长类(largegrowthsector)的299只共同基金,在过去的5年或10年中,每年年均表现都比标准普尔500指数低大约300个基点。10年中300个基点的差距(基金的5.6%与指数的8.6%相对应)意味着,如果将1万美元投资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它将增长到22755美元外加分红;但如果将相同的数日投资于大市值基金,却只能增长到17309美元,这就产生了24%的差距。接近1.5%的费率和超过100%的换手率所引发的巨大的交易成本,都间接导致了共同基金整体表现不佳。更糟的是,这个结果并未将购买过程中任何的附加费和已实现利润的资本所得税所产生的影响考虑进去。
这些结果可能比较令人沮丧,而实际的成绩记录更加不容乐观,因为这个结果仅仅反映出在研究期间得以存活的基金公司的表现。如果我们把那些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基金公司也考虑进来的话,那么这些基金与平均市场表现的差距将比此前呈现的数据更糟。
2004年,普林斯顿的伯顿·马尔基尔(BurtonMalkiel,即《漫步华尔街》的作者)对1970年以来的所有共同基金进行了研究,其中共有139只基金维持了30年以上。他发现,76只基金的年均表现低于市场水平1%以上;只有4只基金的年均表现比市场平均高2%以上。马尔基尔的报告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指出,截至2003年,在理柏分析服务公司(LipperAnalyticalService)评估的大额基金中,超过80%的基金在过去10年中都不及标准普尔500的收益。马尔基尔同时还指出:“几乎没有基金可以持续高于市场表现……10年又10年,某个时期最好的基金也许到了下个时期就成了垫底的……我们不可能提前预测到哪只基金将会有良好的表现。”“在这里,同样由于只考虑了存续下来的基金,整个结果实际上被高估。
即使有证据能证明大多数共同基金确实表现欠佳,那么有没有基金具有不断超越市场表现的能力呢?如果有,我们有办法提前辨认出它们吗?近期的两个研究为这种能力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这种能力被提前辨认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科索斯基(RobertKosowski)同三位合作者于2006年12月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对1975~2002年的共同基金产业进行了研究。运用了一系列的绩效评估模型和我们所知的自抽样统计方法后,他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基金经理都很善于择股,收益足以弥补其成本。另外,这些经理人所获得的优良阿尔法值都有一定的持续性”。随后他们继续论证,“我们的自抽样检验一致表明:排名前10%的基金所显示的较大的正阿尔法值在扣除成本后,极不可能仅仅因为样本变化(运气)而增加。”
就算确实存在技术高超的基金经理,我们能够事先把他们找出来吗?2006年,波士顿富达研究所的W.V.哈罗(w.V.Harlow)和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McCombs商学院的基斯,布朗(KeithBrown)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一方面证实了一般的基金经理只能在不到一半时间中有超越市场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使投资者发掘出优秀职业经理人的概率达到60%”的选择过程。
哈罗和布朗表示,大多数基金经理能否超越某些基准并不是他们要研究的问题。他们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可能事先找出那些能够抓住有利机会并创造突出的风险调整绩效的基金经理?”8哈罗和布朗找到了一系列用于解释过去卓越表现的因素,尤其是在成本和换手率方面,但他们最重要的成果在于证实了科索斯基的研究,即具有这些特征的基金经理有将其卓越表现持续下去的趋势。换句话说,过去的阿尔法将会成为其未来值的预测。
这两篇论文似乎都否定了之前那些对共同基金的研究得出的大量令人沮丧的结论,而且这些论文都为他们各自提出的正面论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支持性论证。科索斯基等人提供了一部分基金公司表现卓越的证据,但是除非投资者能事先找出这样的基金经理,否则这些信息将毫无价值。哈罗和布朗的论文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支持。
人们通常会质疑,哈罗和布朗是已经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还是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哈罗和布朗的研究建立在基金过去表现的数据库基础上,这意味着投资者并没有得到能预先确定其基金经理的模型。当然,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当投资者用哈罗-布朗范式确认出基金经理后,他们的表现会如何。而且,如果对投资者而言选择基金经理的过程变得如此简单,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就会被新注人的资金造成的雪崩所埋葬,而不再去寻找他们实现卓越表现的投资战略。不论他们的技巧或风格如何,每个基金经理都会有一个最高限制,也就是为什么管理层在一定的时候会停止新资金的注人以防止这种雪崩的发生。倘若雪崩真的发生了,知道基金经理们过去的技巧对于投资者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已不再是这些基金的持有人了。
共同基金悠久的历史显示,即使短期的卓越表现也能够吸引到足够的新资产来扩充其管理下的投资组合。管理的资产增加了,交易成本随之增加,职业经理人的优势也就开始被削弱。
接下来,我们看看对冲基金产业的问题。该产业宣称它有很好的表现,其成功管理所带来的丰硕回报吸引了大批华尔街上的最睿智人样。如果某人能够得到一个超越市场表现的好机会,且在风险调整后具有持续性,则它最有可能被运用于对冲基金之中。与传统管理工具相比,对冲基金的运作限制更少,这意味着对冲基金能够通过所能找到的任何机会获利,而没有“大型资本”、“高回报率”或“国际资本”等的操作限制。它们卖空和买空的权力也赋予了它们以套利来赚钱的机会,即卖空它们认为被高估的资产,买空它们认为被低估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积累大量的小额利润并最终形成巨大的收益。
认知偏差导致的定价扭曲为所谓聪明的投资者提供了大最机会,但在接受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先来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计算对冲基金击败市场的表现不像计算那些共同基金或长期基金那么容易,不像股票和债券,在对冲基金中是没有“市场”的。那么怎样才能说这种基金超越了市场表现呢?它们有可能超越某个随意界定的基准吗?比如在国债收益率上加一定的百分比基点。然而,真实的结果往往更像凌乱的数据或幸存偏差。
第二,计算对冲基金风险是一个有争议的过程。传统投资管理中所采用的用波动率来度量风险的方法在多头/空头环境中不再适用。另外,对冲基金收益率易出现肥尾现象或尾部风险,即出现极端负收益的概率高于正常水平。对冲基金是卖空者,而卖空者面临着发生无限损失的风险(因为股票价格只能跌到零,但可以上涨到无穷大)。它们或许会陷入我们所知的“轧空”闲境,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由于借不到股票,于是就无法交割它们卖掉的股票。结果是,它们被强迫回到市场中以很可能高于它们出售价的价格买回这些股票。
许多对冲基金只包含非流动资产或只能在很小的市场中交易的资产,而在这些地方发生巨大损失的概率远远大于普通股票的投资,例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灾难性经历。日当基金公司有外债时,其所有活动的风险都变得更大,这是经常应验的。
根据定义,大多数投资者无法超越市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市场。另一方面,可获证据表明,如果市场竞争越激烈,则投资者不容易超过其他人而获胜。大多数人知道的信息已经反映在了价格中,而以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方式进行思考并非易事。
杰克,特里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先驱之一,《金融分析师杂志》的长期编辑,他认为系统性错误为赚取超额利润提供了许多机会。他最真欢把他认为特别有吸引力的股票告诉大家,如果大家马上就赞同,那么他就知道该股票的价格已经反映出了他的想法,然后他就继续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但如他的朋友们不接受,他就有很大的动力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并极有可能进行投资。
特里诺是一个不喜欢与人来往的操盘手,他偏好他所谓的“慢主意”,即这些想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果,因而这些主意对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没有吸引力。在时间跨度比较短的情况下,有经验的投资者通常会迅速行动,不给其他人留下任何机会,因为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正如保罗·萨缪尔森说过的,“没有飞来横财,也不存在肯定的收益”。这就是富勒-泰勒公司要在小盘股中寻找机会的原因。如果大盘成长型共同基金的组合能在扣除税收和费用之前,以勉强超越市场的成绩过关,则赚钱会更容易而收益也将变得更确定。
不过,这个结论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限制条件。这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限制条件是关于单只证券的套利问题;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则涉及整个市场的无效性,这与单只证券的无效率是相对立的,而且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连。
在整个资本理念和行为金融基本原理的争论中,套利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套利意味着在买入一项资产的同时出售掉另一项资产,并期望他所买入的资产价格会上升而他卖出的资产价格会下降。例如,通常同种证券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市场进行交易,或者证券在一个市场以常规有价证券的形式参与交易,而在另一个市场以衍生证券(如期货)的身份出现。如果在两地证券价格不同,则套利者买入低价资产而卖出高价资产的行为将使两个价格趋于一致。这类例子中的套利实质上是无风险的交易。
有时候,两项资产相互联系但并不精确地相关,例如股票和以其为标的的衍生证券,在这些情况中套利也将有机可乘。可转换债券和它所转换成的股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更具风险的策略就是在两个特征相似的有价证券之间进行套利,例如在两个高科技公司股票之间套利,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是许多对冲基金的最爱。的确,有效市场假说的很多案例中都假设套利是十分重要的,并用它来解释为什么价格不一致现象会十分短暂,为什么超越市场会如此困难。
如果套利机会确实总是存在,而且套利者也总能发现这个不一致性,并在不承担仟何风险的条件下立即消除定价错误,那么对投资者理性行为的假定就将成为有效市场假说中第二重要的问题。由于套利现象普遍存在,这一系列条件就成为了我们所知的无套利条件,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套利机会是不存在的。
在无套利条件下,资本理念和行为金融基本原理之间的争论也随之消失。不管是什么原因,错误的定价都会迅速消失,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可能享受到它带来的任何程度的好处。也就是说,行为金融所描述的异象可能突然出现,但在任何主动的经理人能利用其赚钱之前,异象就将消失。
作为资本理念中最突出的学者之一,斯蒂芬·罗斯(StephenRoss)以十分肯定的语言描述了无套利对此争论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人们(包括我自己)都不能在行为上完全理性。相反,人们的所作所为经常让我感到惊诧,但这并不是金融理论的重点。无套利要求聪明并且拥有充足资金的投资者在套利机会出现时将它们消灭……新古典理论是贪婪者的理论,而非理性人类的经济学,这就是金融与传统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区别。资金充足的套利者发现了这些机会(由行为偏差产生)并一拥而上,利用他们的行动消除这反常的价格差异。
哈佛经济学家安德烈·施莱弗(AndreiShleifer)和泰勒在芝加哥的一位同事罗伯特.维什尼(RobertVishny),在一篇有着深远影响的论文——《套利限制》(TheLimitstoArbitrage)中,对罗斯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施莱弗和维什尼重点描述了教科书中的世界同投资者进行决策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在教科书中,金融市场上的套利没有资本要求也无须承担风险。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套利都需要资本且风险很大。另外,专业化的套利都是少数专业投资者通过运用他人的资本来进行的。这种专业化的套利在证券定价方面有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应用含义,其中包括套利在价格极度远离基础价值这种极端情况下变得无效。该模型同时还指出了金融市场中何处容易出现金融异象以及套利为何无法消除它们。”
简而言之,真实的世界并不像有效市场假说或罗斯的论断中描述的那么简单。如施莱弗和维什尼所指出的,大多数的套利行为并不是大量投资者发掘错误定价的过程,而是少数拥有复杂专业知识的投资者运用策略来管理大量资金的过程。这些套利者充分认识到存在的风险后,可能会旁观,或者有时会参与其中并使得价格偏离更加严重。套利通常需要进行卖空交易,而这往往具有较大的风险和较高的执行成本。由于一些噪声交易者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这就使得本应相等的价格继续发生更严重的背离。对于套利者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动量风险(momentumrisk),即当其他投资者仅仅因为股价上升而追涨时,这种涨势就被一波接一波地向上推动,巨大的价格泡沫也随之被积累起来。“顺行情交易”(Don'tfightthetape)是华尔街上的一句老话,但不论何时都会应验。
另一方面,尽管套利的限制乃至有效市场的维持非常重要,并且有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仍须认识到这个性质没有什么实质意义。比如,荷兰皇家石油(RoyalDutchPetroleum)的两部分前身——美国的荷兰皇家集团(RoyalDutch)和伦敦的壳牌运输(ShellTransport)——它们的标的资产是完全相同的。按照汇率换算后的资产份额,荷兰皇家集团的权益价值是壳牌运输的1.5倍。然而,按照这个标准,荷兰皇家集团相对于壳牌来说被长期低估了35%。
另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MCI通信(MCICommunication)的案例,其在纳斯达克的代码为MCIC,并且日交易次数是万通投资公司(MassmutualCorpo-rateInvestor,MCI)的1000倍;MCI是一个封闭式基金,主要投资于公司债券,但也恰好有MCI的股份。这两个公司之间显然没有什么联系,但从1994年下半年到1997年下半年,尤其是最后的12个月内,MCI发起了一场收购的谈判,其股票每日价格与交易量的波动出现同向变动的趋势。在对这个投资困惑的案例进行研究后,其研究者指出,“MCI的大部分交易都来自于那些无意进行股票交易者的行为,而且他们极有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交易的发生。”
那么套利者为何未能步调一致并阻止两只证券的同向运动呢?这是因为这些狭小市场上的证券很难借到或存在很高的成本。于是,在特殊案例中,定价的不一致可能会持续铰长时间,而且大家都可以发现在这里有效市场假说不再成立。
这些异象十分有趣,它们反映出在大多数市场情况下无套利条件很难得到满足。这样有前景的机遇听起来十分诱人,但我们却很少能碰到。
在另一大类体现出市场无效性的案例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套利限制,它被称做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定价,而非某些单一证券的定价错误。该现象有一个更常用的名字——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我们将在第6章从另一个角度展开对此问题的讨论。
这些市场非效率的案例已过去很久了,但它们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1928年中期到1929年10月,股票价格上涨了50%;而1932年6月又出现85%的大幅下降;在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中,股价一天之内下跌20%;1998年夏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陷人濒临破产的危机,使得整个金融系统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从1995年年末到2000年10月,股价出现140%的增长,却在2003年2月出现44%的下挫。
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定价并不一定要以繁荣和萧条交替循环的形式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和成倍增长的利率使得资产价值几乎创历史最低,而股利收益率接近历史高位。这使投资者们每天提心吊胆。1979年,在忽略了通货膨胀对公司负债真实价值负面影响的同时,投资者也普遍忽略了通货膨胀对公司资产价值和公司货币收入的正面影响。131981年,当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最终取得控制通货膨胀的胜利之后,投资者们觉悟了。资本市场中大量存在的被低估的资产,使得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最持久的牛市之一。
有些无情的人们不断提醒着大家市场是普遍无效的,然而被人们称做“理性泡沫”的现象又是引起市场非效率的另一大的原因。“理性泡沫”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十分聪明的人们——所谓的“理性投资者”挑中了噪声交易者为他们制造出的错误定价的资产——他们假设这种不合理的繁荣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并认为自己会很聪明地知道如何及时退出,于是就随着人群进入泡沫中。
聪明的投资者合理地利用这些理性泡沫已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麻省理工的彼得·泰明(PeterTemin)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的Hans-JoachimVoth研究了一家伦敦的大银行——Hoare银行,该银行在1720~1721年间就安然渡过了著名的南海泡沫。那个时代的著述表明南海公司根本没有足够的收益来证明其泡沫价格,但Hoare银行一直购买该股票直到1721年8月清算头寸。泡沫在10月破灭。
普林斯顿的马科斯·布鲁纳米尔(MarkusBrunnermeicr)和斯坦福的斯特凡·内格尔(SteganNagel)对近期纳斯达克泡沫的研究表明,它跟Hoare银行的症状十分相似。那时候,许多对冲基金都重仓持有科技股,到1998~2000年间泡沫表现得十分明显。但这些基金集团,在价格暴跌之前都得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一只一只地进行减持。结果,这些基金由于其超越基准的表现而变得十分热门。布鲁纳米尔和内格尔得出一个结论:“短期(在非理性环境中)利用价格泡沫对于理性投资者来说是最优策略。”











